
“現在,你們造車的人是不是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學造車的了?”那天見到智己汽車的CEO蔣峻,我跟他開玩笑地說。他的反應也挺快的,回答得跟真的一樣:“是的呀,現在造車的好像不用懂內燃機原理,只要懂第一性原理就行了。”
28年前,蔣峻大學畢業就進了上汽集團下屬的齒輪機廠,一路干過技術、供應和市場等很多崗位。2006年,上汽打造自有品牌榮威,經歷了第一次“體制內創業”的艱難,蔣峻也參與其中。2018年底,上汽內部秘密組建了一個代號L的“一號工程”項目組,籌劃生產高端智能汽車,蔣峻被抽調為籌建組組長,與他搭檔的還有當年在榮威時的品牌總監劉濤等人。
當時,馬斯克將在上海開建特斯拉超級工廠的消息已經傳得甚囂塵上。“對手的軍艦都開進吳淞口了。”蔣峻對我說,“我們的反應還是慢了一些。”
就在本月,L項目終于揭開了面紗。汽車品牌被定名為“智己”,取自于《周易》。投資人分別是上汽集團、張江高科與阿里巴巴,創始輪融資金額即達100億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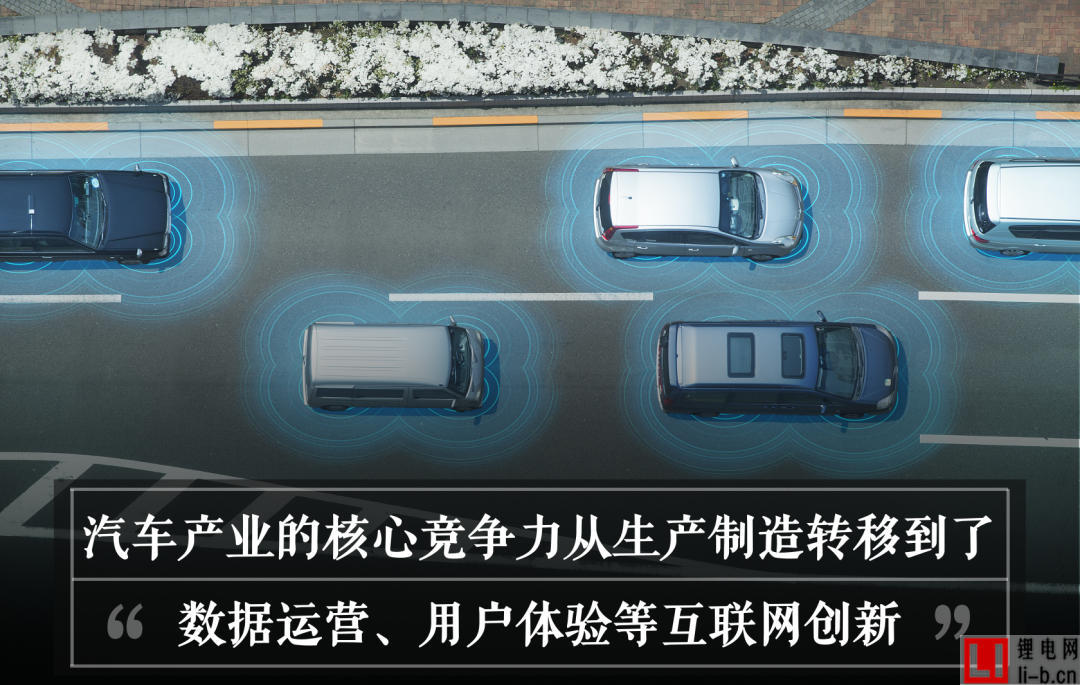
蔣峻、劉濤等人,都算是打過硬仗和死戰的業內宿將。他們這一代汽車人見證了中國汽車產業高速發展的激蕩歷程。但是,近些年來的智能造車狂飆,還是令他們有點眼暈目眩,且不說打到家門口的特斯拉,即便是國內的造車新勢力,也帶來巨大的觀念和感官刺激。
一部百年汽車史,就是一次又一次的、頗為符合“康波周期原理”的顛覆史。汽車自從1886年被德國人本茨發明出來之后,先是在1908年被亨利·福特的T型車引爆了一場大革命,并讓美國從此成為“車輪上的國家”。到1960年代,日本豐田又用精益管理模式再一次實現了突擊勝利。
中國人最早造車的是東北軍時期的張學良。新中國成立之后,紅旗車的誕生成為國慶十周年的“十大獻禮工程”之一。1978年改革開放,上海汽車廠與德國大眾合作的桑塔納轎車,是當時中國最受關注的外資引進項目。
2009年,中國的汽車產銷量,歷史性地超過美國,成為全球第一造車大國,這是中國當代制造史的一個標志性事件。也是在這一年,新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考察陷入泥潭的汽車產業,他沒有趕赴三大汽車公司總部所在的“汽車心臟”底特律,而是飛到硅谷,去參觀了馬斯克的特斯拉工廠。
戰略性的拐點,便在那一刻戲劇性地發生了。
“從我們讀大學到進上汽,這幾十年來,都覺得BBA(奔馳、寶馬和奧迪)高高在上,可以被追趕,很難被超越。可是,智能汽車的出現,似乎讓這個產業的某些基礎性規律被更改了。”蔣峻很感慨地對我說。傳統車企積累了近一百年的內燃機技術優勢,在新的電動模式下蕩然無存,發動機瓶頸消失,汽車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從生產制造轉移到了數據運營、用戶體驗等互聯網創新。
克里斯坦森在《創新者的窘境》中,研究過這一革命發生時的可怕景象:破壞性技術是一種革命性的技術創新,其技術產品是從未有過的、完全新興的事物。而對于大公司而言,這一技術在一開始往往針對的是一個無法檢測的新興小市場,它不能滿足大企業的增長需求和強大的制造能力,這對大公司的決策構成了致命的挑戰。更陌生的是,在誕生初期,破壞性技術產品的性能,要低于主流市場的成熟產品,但由于其某些新特性,使得這種產品會受到非主流消費者的喜愛,終而徹底改變了市場的價值主張。
從喬布斯到馬斯克,無一不為克里斯坦森的這些觀察做了最生動的注腳。
而對上汽和蔣峻等人而言,從引進的桑塔納,到自主的榮威,再到今天的智己,進化的曲線似斷非斷,灰蛇千里。在資本和組織架構上,上汽集團對智己的規劃是縝密周全的。它的制造環節將由上汽的工廠完成。早在2015年,上汽就與阿里開始了“斑馬智能”的業務合作,成為了上汽集團智能化探索重要節點;未來,上汽集團在技術、體系、資源等諸多領域的優勢資源都將被率先應用在智己汽車上。而智己的研發基地將設立在張江,那里是今年新確定的中國四大科學中心之一。
還有一個不小的突破是,在智己的股本結構中,管理團隊擁有了10%的股權,這在大型國企中十分罕見。在與我的交流中,蔣峻重點談及了智己的兩大突破。
其一,當然是技術。智己汽車打造全新的電子電器架構,從底層打通整車與駕乘體驗高度相關的ECU控制器,將客戶場景和汽車感知充分融合,鼓勵用戶進行高度自定義,實現汽車智能化寬度和深度的全新突破。上汽與寧德時代在電池技術上有深度合作,智己汽車的電池包是零自燃標準,用最嚴苛的側碰針刺標準也不會燃燒,被稱為“永不自燃的安全電池”。即將在明年四月面世的第一代智己汽車上,將全球首次量產裝備11KW大功率無線充電的裝置,在充電效率上和有線充電幾乎沒有差異。
蔣峻還告訴我,智己在續航技術的“能量密度”上,將超過目前國內同行30%以上,全新架構帶寬內最高可支持近1000公里的續航。
其二,在我看來,更具想象力的是,智己提出了打造“用戶價值企業”的新主張。蔣峻舉了一個例子。你開車從家里到公司,途中的路上有一個坑,你做了一個減速通過的操作。智己汽車就會把這個數據傳輸到后臺,當你下次開車經過這個坑的時候,汽車將會自動識別。而這個數據又會共享給所有的智己汽車用戶。也就是說,你發現了一個“坑”,并貢獻了一個數據節點。那么,有沒有某種方式對你的貢獻進行價值化獎勵?
智己團隊的一個大膽構想是:以公司股權為價值池,通過區塊鏈的技術,讓用戶貢獻的每一個數據——行車數據、地圖數據、交互數據等等,都可以被量化積累,最終體現為用戶“數據賬戶”上的資產。
如果這個構想得以實現,那么,即將面世的智己汽車就將是全球第一輛能夠生產數據、并因此獲得利益的“智能移動工具”,它的使用者兼具了消費、“參與制造”和受益的三重屬性。數據成為創造價值核心的生產資料,用戶也成為供應鏈、價值鏈,包括制造等等方面的驅動者和“共創者”。
聽著蔣峻的描述,我突然意識到,這位有28年造車閱歷的汽車人的腦子里,似乎已經被植入了一塊互聯網的基因芯片。





